从1=0.99999…开始的无穷问题
系列文章:
引题
1=0.99999… 吗?此问题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网络社区里出现了无数多次,每次都能引来上百人激烈的争论,可谓是最经久不衰的老问题了。这里我就不再引述了,感兴趣的话直接搜索即可。
这本质上是实无穷与潜无穷之争。
人们对于无穷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潜无穷,一种是实无穷。
实无穷思想是指:把无限的整体本身作为一个现成的单位,是已经构造完成了的东西,换言之,即是把无限对象看成为可以自我完成的过程或无穷整体。
潜无穷思想是指:把无限看作永远在延伸着的,一种变化着成长着被不断产生出来的东西来解释。它永远处在构造中,永远完成不了,是潜在的,而不是实在。把无限看作为永远在延伸着的(即不断在创造着的永远完成不了的)过程。
很明显,1 对应实无穷,0.99999… 对应潜无穷。
我们可以把问题转化一下,将二者相减,看差值是否为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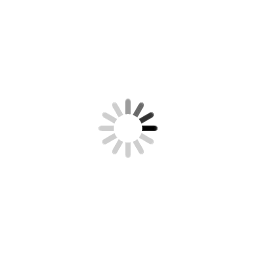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其差值结果自然是,小数点后面跟无穷个“0”,但问题在于,最后的那个“1”在哪里?何时才能写那个“1”?
写不出来是吧,从过程看来,写出来的都是“0”,不是吗?
那这和“0”有什么区别呢?我同样可以在“0”的小数后面加上无数个“0”,这不就一样了吗?
是不是感觉很别扭,有什么地方不对。
芝诺悖论
别扭就对了,那些数学悖论就是这么搞得。
比如大名鼎鼎的芝诺悖论,就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提出的一组悖论,其中的几个悖论还可以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物理学》(Physics)一书中找到。最有名的是以下两个。
阿基里斯与乌龟的悖论(Achilles and the tortoise Paradox):在跑步比赛中,如果跑得最慢的乌龟一开始领先跑得最快的希腊勇士阿基里斯,那么乌龟永远也不会被阿基里斯追上。因为要想追到乌龟,阿基里斯必须先到达乌龟现在的位置;而等阿基里斯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乌龟已经又前进了一段距离。如此下去,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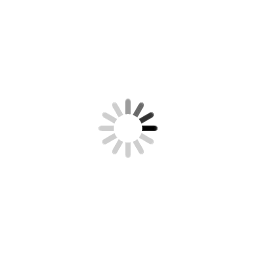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二分法悖论(Dichotomy Paradox):运动是不可能的。你要到达终点,必须首先到达全程的 1/2 处;而要到达 1/2 处,必须要先到 1/4 处⋯⋯每当你想到达一个点,总有一个中点需要先到,因此你是永远也到不了终点的。其实,你根本连动都动不了,运动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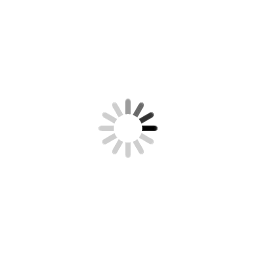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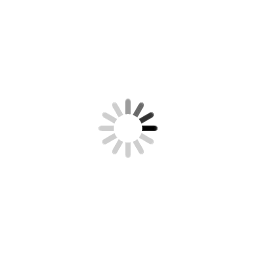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类似于当下的等比数列求和会不会等于1的问题:1/2 + 1/4 + 1/8 + 1/16 + …
或者说,你想回家,必须先经过总路程的二分之一,然后再经过剩下路程的二分之一,再经过剩下路程的二分之一……如此继续,你会永远到不了家
这样一来,此物体将永远停留在初始位置(或者说物体初始运动所经过的距离近似0),以至这物体的运动几乎不能开始。即:由于运动的物体在到达目的地前必须到达其半路上的点,若假设空间无限可分则有限距离包括无穷多点, 于是运动的物体会在有限时间内经过无限多点。
数学中的无穷小量问题
芝诺悖论里面涉及动与静,常量与变量,连续和离散,有与无的关系,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等诸多关系。
比如上面的例子中,左边的“0”代表“无”,右边的“0.00000…000…?…(1)”,不管这个“1”何时写,总是代表“有”吧,总不能一个大于0的正数会缩小至0吧。
所以,问题就被简化为:“无穷小”是否等于“0”的问题。
这就是“有”和“无”的过渡,量变是如何引发质变的。这就是“0”与无穷小量的辩证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第二次数学危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无穷小量是零还是非零?如果是零,怎么能用它做除数?如果不是零,又怎么能把包含着无穷小量的那些项去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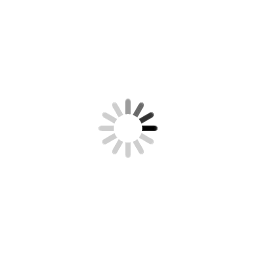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这些问题也可以这么转化:
无限趋近的两个点何时可以视为同一点,这是连续和离散的辩证问题(其实搞明白了这一点,实分析中的“实数集”也就是数轴的连续性就明了)。
两个点的逼近过程可视为一种运动,那运动又是何时变成静止,这就是动与静的辩证问题
若运动视为变量,静止视为常量,这也是变量与常量的辩证问题(极限的收敛性同理)
从极限的观点看,“无穷小量"就是极限为零的变量,在变化过程中,它可以是"非零”,但它的变化趋向是"零",无限地接近于"零"。
芝诺悖论的巧妙之处在于——将有限的长度分成了无限多份,把无穷的概念嵌入有限之中。要知道,在有限的范畴内,1+1=2;而在无穷的范畴里,∞+∞≠2∞;但芝诺悖论有意思地将两个不同概念集于同一个问题。
其实,从实际出发,这些所谓的悖论都不是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对人来说,这是一种悖论。
所谓的“悖论”无非是在思考人类二元概念名相的边界问题和相互转化问题。因为人类的认知局限性和相对性,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无穷的,无论借助于什么样的经验、观察抑或知识。我们对极限、无穷小的认知都很难摆脱固有的静态直观场景,本能的需要眼见为实的身临其境体验,即使我们短暂地理解了,也被日常场景冲淡。所以,1=0.99999…这种问题才是经久不衰。
我们口中说着“无限”,实际上大脑所想像的,都是通过日常经验所积累的有限概念,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一种有限的相对认知,这是认知本身的局限所决定的。
西方现代数学的解决思路
现代数学微积分的极限概念,就解决了这个芝诺悖论的问题,也就是无限分割后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总和 —— 可以是有限的。
对0进行无限累加,则始终是0,对无穷小进行无限累加可以是有限的常量。
解决这个问题的柯西,使用的是(ε-δ)语言极限的定义,这种语言可以说是让人十分头疼,学过《数学分析》的人都清楚。
而且他对无穷小量进行了新的数学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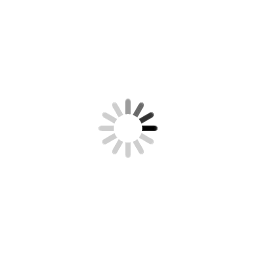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它的解决思路基本是这样:不再将无穷小量视为无穷小的数,而是一个要多小有多小的数。也就是说,不把它写成一个具体的数,比如无穷小量 = 0.00000001 ,而是让它的值在同样的计算过程中保持未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极限,如果说极限为 0 ,就是无论你给出一个多么小的数,极限都比这个数小,但没有人知道极限或者无穷小量是一个什么数。
这个方案不算错,但我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解决人的认知感观上的矛盾之处,而是用一种人类无法从直观上去感受,只能通过抽象概念去死记定义,然后逻辑推理,这种认知方式某种意义上是反人性的。
而且无穷小量可以用添加定义来解决,但动与静,常量与变量,连续和离散,有与无的关系,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等诸多现实关系,又该如何解决?再定义吗?还是干脆使用数学来代替日常语言。现实他们就是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能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看得人晕头转向的物理公式海洋,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这就是宇宙真相。
另一种数学体系
万幸,世界存在另一种数学体系,没有那么多概念定义,有的只是实际的问题解决方式,但神奇的是除了古文符号的语境不适应之外,我竟然能完整的将整个微积分的思路彻底清理,而且这个过程如丝一般的顺滑,没有所谓的数学危机,更没有多余的数学定理,和添油加醋一般的数学符号。
更重要的是这种数学体系的代表作竟然是——中国版的《几何原本》。
惊不惊奇,意不意外。他们都说中国版的《几何原本》是从西方的《几何原本》翻译过来的,可为什么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西方科学发展是建立在两个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希腊哲学家们(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哲人没能走出这些步骤大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学]发现。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美国的一位学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
我认为,古代中国存在另一种科学范式,而且更适合我们,只不过他们都隐藏在古籍之中,等待我们去发现。
谁说西方伪史论是没用的,我发现这一点正是由于@程碧波先生的国计学(比如“程碧波:纹明,《几何原本》来自中国的证据及其在西方的错误传播”一文),而他对中国版的《几何原本》的解读让我看到了世界上的另一种可能。西方伪史论有许多好东西啊,有时进步和创新就在于换个角度看世界,视角切换后便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之意非是让大家认同程碧波先生的观点,而是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范式是怎样的,这一点对我们的现在和将来至关重要,什么是科学革命,就是科学范式的转变。
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不纠缠于那些宗教式的形而上学理论,比如下面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共识。不过这样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基督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说基督是神,那就同时存在上帝和基督两个神,也就不是一神教了;如果说基督是人,那神的儿子是人,岂不是很不合理。如果说基督是人,又怎么可能死了之后再复活?如果耶稣不能复活,普普通通和常人没什么区别,那又为何要信耶稣呢?
…正因为这个问题,基督教内部争论不休,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东西教区分道扬镳,罗马帝国风光不再,如果不是法兰克帝国,基督教的命运真不可想象。
选自《浅析基督耶稣的本质问题对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影响》
更不要说,因为教法理念不同,那一神三教相互之间杀的昏天暗地,其内部也相互争斗不止。
对中国人而言,这是纯粹吃撑了没事干吧,但你们的农业并不发达啊。其实,与西方的宗教争斗相类比的,是中国的政治斗争,天无二日,改朝换代。这是东西方文明发展模式的不同所导致,这一点我会单独开章节论述,这里就不详述了。
说回正题,下面我阐述一下,中国版的《几何原本》所展示的中国数学思想是如何在纠缠于那些宗教式的形而上学理论,进而解决这个“芝诺悖论”问题的:
很简单的,中国式的微积分,实际上是一种“微分”与“积分”的镜像对称。
“微分”是“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谓一尺长的捶杖,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是日取其半,总有一半留下,万世都取之不尽。(很明显,这是“芝诺悖论”的变种形式。)
“积分”则是“微分”的逆向过程,再将这分割的无限小的“捶”,再积累起来,恢复成完整的“一尺之捶”。
这两个过程是对称的,你怎么分割,就怎么积累。所以,不需要定义什么高阶无穷小、低阶无穷小之类的,同阶的无穷小可视为同一种分割尺度,这些都是相对概念,相对之下,分割过高则是高阶无穷小,分割过低则是低阶无穷小。一切都是相对的概念,脱离微分谈积分,或者脱离积分谈微分,都是一种思想的不完整性,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完毕。
是不是很简单,实际上祖冲之的“割圆术”就是这样的思路,先分割再拼接,这就是微积分。
不要小瞧这一点,以为这个过于简单了,其实简单反而说明,这个才实用,太复杂的东西反而不实际。
按这种思路,我们根本就没必要讨论“无穷小”是否等于“0”的问题,因为“无穷小”是中国式微积分的一种尺度无限分割过程,在人的认知想像中,可以理解为一把刻度无限精确的尺子——实数轴的实体化,而无穷小,指的是尺子上的某一线段。
没错,是“线段”,而非“点”。线段的微分是无限小的“线段”,这些线段相连才是原有的完整线段。
从测度的本义来看,正如中国版《几何原本》所说,直线不是点的集合,直线只能是线段的集合,因为点只是线之边界,点的长度为0,任意无限多点的集合,其长度仍然为0。长度无穷小的线段跟长度为0的点,有天壤之别:前者可以通过无穷累加而成一非零数值,后者则无论如何累加均为0。线与面、面与体的关系亦同理可推。只有在有限项相加时,高阶无穷小项才能等价于0。实分析混淆0与无穷小,认为线段的测度为点的测度之加总,面的测度为线的测度之加总,体的测度为面的测度之加总,违反了中国版《几何原本》“一点无分亦非几何,即不能为线之分也。一线无广狭之分,非广狭之几何,即不能为面之分也。一面无厚薄之分,非厚薄之几何,即不能为体之分也”的阐述,必然会出现逻辑矛盾。
如今的“几何学”翻译有误,应该翻译为“规矩学”或“图形学”。“几何”在中国版《几何原本》是一种“测量”概念,数从测量尺度而出,“几”是测量长度的刻度模样,“何”为“负荷”,即“测量值”。相当于现代分析数学中的测度论,“度”即是指“度量衡的刻度”,“几何”即是指“相对某特定刻度的可测量”,换而言之,“几何”就是——(在某度量下)“数值是多少”。
如此一来,“无穷小”是否等于“0”这一问题,便有了实际的意义和结论,“等于”之意是从测度出发,询问二者是否为同一数值,而某“微分”也就是无穷小量,在没有对应的“积分”无限累加时,测度为0。但无穷小量是可以作除数的,并不能当作“0”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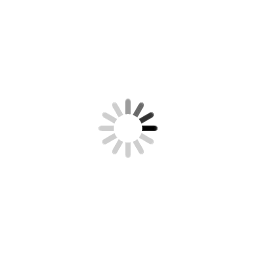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如此一来,就不存在所谓的“数学第二次危机”。
而且,既然线段的微分是无限小的“线段”,这些线段相连才是原有的完整线段。如此一来,还需要证明实数的连续性吗?
而且,“线段”的无限可分,康托尔构建的这种“分形”三分集合,就不必搞什么集合论作为数学公理体系的基础,进而也不会有罗素悖论来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康托尔集合的本质是一种类原子论的离散思想,集合论的提出就是为了定义无限,为了解决实数集与点的无穷关系,实数集有无穷多个点,这些点无法与自然数集一一对应,最后认为实数集是不可数的(不可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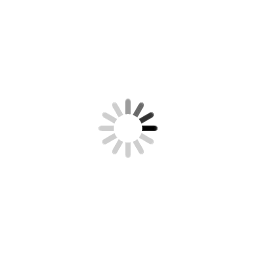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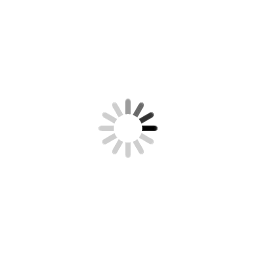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能很明确的看出,两个体系的思维不同,西方偏离散,中国偏连续,离散会导致阴阳概念的绝对化和对立化,连续会导致阴阳概念的相对化和统一化)
因为按中国学术思想,整个体系就不是建立假设的公理体系之上,而是实际的测量体系之上。
在中国的数学体系语境下,也不存在什么实无穷与潜无穷之争,微积分的镜像对称特点本就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无穷的特征:“微积分”的无限分割和积累给人一种无限的过程性,这就是潜无穷,但无论再如何分割和积累,数还是那个数,不会改变,这就是实无穷。这两个观点不过是站在不同的视角所得出的结论,都对,又都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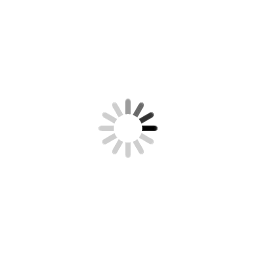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中国的学术体系都是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西方其实也是,只不过他们的问题和需求更多倾向于一种绝对理性的逻辑框架构建,而中国则偏于实际应用,不搞那些有的没的,这是文明哲学偏好不同。
现代数学体系的基础问题和漏洞有许多
举回原来的例子,回到最开始的主题,1=0.99999…
按现代数学体系,这个问题还可以转化为:实数区间 [0, 1] 与 [0, 1),这两个实数区间是否相等(该怎么理解和解释这种“相等”呢)。
很明显,[0, 1] 与 [0, 1) 是不同的实数区间,很明显第二个实数区间少了一个点——实数1。
很明显这是“无限趋近的两个点何时可以视为同一点”疑问的变种模式。任意两个离散的点之间,都有无穷的点,这并不难理解。用无穷小量去解释是无效的,因为解决不了人们心中的感观和理性的矛盾和冲突。
这里的问题关键,其实是——什么是点?
1个点是1个0 维的对象。点作为最简单的图形概念,通常作为几何学、矢量图形和其他领域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点是无法被定义的。试图去定义点就会陷入重复定义、逆逻辑定义的深渊。点作为原始概念的同时也具有原始概念的性质。
比如,把平行四边形定义为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因此就必须先对四边形、平行以及对边进行定义。定义四边形时,应先对多边形及边进行定义,又必须先定义折线,故必须先要对点和直线进行定义。
但是,在一般的初等几何中,点和直线都无法再用已被定义过的概念进行定义,它们都是原始概念。在数学中,点、直线、平面、集合,空间、数、量等都是原始概念。
数学中的点也不是这样的,数学中的点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并不是我们头脑中想象的点,点定义为:没有大小和尺度也不可分割的事物。 点通常作为一种参考对象。
数学上所研究的只占有位置不占有任何空间的“点”,没有粗细的“线”,没有厚度的“面”。
问题在于,他们嘴里说的,和心理想的是一回事吗?
在教科书以及所有的数学理论中,他们大脑中所想像的“点”,都是一种“小黑圆”或“小黑球”,所以才是“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等积分概念。
这种“小黑圆”的“点”是一种“有”,而不是”无“,”无“是想像不出来的,只能付之于抽象逻辑,其实也做不到。没有就是没有,连想像的余地都没有。凡是你想像了,说明还是有的。
这个所谓的”只占有位置,却不占有任何空间“是如何做到的?位置与空间又有什么不一样?可不占有任何空间的话,”点“又是如何积累成”线“,再积累成”面“和”体“的?还是那个问题,“0”累加均为0,到底是如何生成无穷的问题。
想像中的代表“点”的“小黑圆”或“小黑球”,在数轴(刻度尺的抽象)上的具象化则是“无限小”的“线段”,在平面上,则是“无限小”的“小黑圆”,在三维空间中,则是无限小的“小黑球”。他们即占有位置,又占有任何空间,这样逻辑才通畅。
你看,这不就与上面的“直线不是点的集合,直线只能是线段的集合,因为点只是线之边界,点的长度为0,任意无限多点的集合,其长度仍然为0。”相吻合了。
从中国传统数学来看,所谓的点,其原型是量尺上的刻度,刻度相对于任何线段区间,都是边界。刻度本身并不存在实体,只是一种测试标度,所以,刻度只有相对位置,却不占有任何空间。
从点的定义来看,西方人并没有理解这种思想的来源与精华。程碧波先生怀疑是西方的《几何原本》恰恰是中国版《几何原本》的翻译,而不是他们所宣称的相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我们学习西方学术理论时,总有一种别扭感,这是因为名实分离,或者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不相匹配、不相适应。
中国文化是经史传承,经出于史,经不能离史,古人将书典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就是有这样的考量,理论是从实践总结而出的,“名闻而实喻”,用事实来检验理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这世间,真懂的人往往不会迷信,因为知其根源,知其来历,有经验做依托;只有不懂装懂的人反而会照本宣科,不容质疑书上的理论。没有历史经验传承,误解扭曲是必然。
名相概念本身就是人定义的,辅助人理解事物的,不应有绝对的“概念”,即概念实体化。每个名相概念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存在的意义,以及对应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每一个度量都是基于某个方向的归一简化而设计的测量体系,这就是一种单维度的极化,这必然会导致二元区分和对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若是再将这种二元区分和对立实体化,这就是人自己没事找事了。
这个我们稍后会说明。
历史信息的篡改
不要认为中国版《几何原本》上面写着"从泰西翻译过来",就一定如此,对信息和历史的篡改是人家的老本行。
耶稣会与明朝清朝的关系,为何就不能看作是类似于CIA在中东当地政府开展间谍活动,并扶持反对派呢?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历史不过是不断的轮回,不然你以为一个小小的满族,为何会有如此高明的统治技巧和精神控制术,这种技巧是历代所无的,那些传教士真的就只给满清作科学方面的顾问,而不搞其他的?
耶稣会把美洲的文明,杀光、抢光、烧光,怎么到东亚就突然从良了?不同于野蛮的蒙古人,西方世界对各国的文物典籍都有强烈的占有欲,大英博物馆更是号称有着全世界的文物,替世界“保管”它们,梵蒂冈至今保存着玛雅的历书,但是下命令把玛雅的文化遗迹焚烧的也是他们(以上帝的名义),他们真不知道文物典籍的重要性,恰恰相对,他们比谁都清楚,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垄断而不分享出去。
有案可查的第一份专利权出现在1469年,授于一个在威尼斯刚刚定居的德国人,而专利的内容则是印刷术。没错,是源自中国的印刷术。
西欧的第一项专利权源自中国,不了真正了解西欧中世纪史的人会感到吃惊,实际上是很自然必然的事。早期西欧的专利权应该大部分都来自中国。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出生于1452年的达芬奇,一度被称为伟大的发明家,并且他将自己的“新发明”都画了出来。然而,现代已经有人指出,达芬奇的这些图稿,与一些在当时流传入西欧的来自中国的农书高度雷同,目前大英图书馆内还保存着一本那样的农书。
前面已经指出,西欧的中世纪史从内部看是一部拥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商人与特权贵族的斗争史。而那时的商人主要是搬运和贩卖来自亚洲的商品,主要是中国。在搬运中国商品的同时,也搬运来了中国文化。最初商人的单个规模普遍不大,主要是以行会的形式来获取和维持特权。但是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导致行会逐渐沦为一种阻碍新产品新技术应用的桎梏。新的商人要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必须获得不受行会特权制约的新“特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利权。
但是,在专利权的早期,大多数专利更多是来自对中国的抄袭。也正是西欧人的专利思维,导致中世纪中国文化流入和影响西欧的事实一直被掩盖。想想看,那位将来自中国的印刷术作为自己专利的德国人,会告诉大家这玩意其实来自中国吗?不但不会,而且会消除一切资料,说这是自己发明的。达芬奇同样如此。
明白这个背景,就能明白后来德国的莱布尼茨,为什么谎称自己“发明”二进制是在看到邵雍的八卦图之前。邵雍对易经64卦的排序正是按二进制大小来排的,莱布尼茨的发明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卦象中阴阳符号改成0和1。而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资料证明,莱布尼茨看到邵雍的卦图的确在其发表二进制之前。
西方文明的问题不是“伪史”那么简单的造假,而是从文明根基上的“偷天换日”,如果我告诉你“耶稣”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而是一个人为虚假制造的“神话”,是山寨异教太阳神教(密特拉教,在中东-西亚地区广为流传)的神话,整本《圣经》绝大部分都是剽窃和魔改的,充满着大量的占星术话语,你就会对西方的造假能力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古埃及与上古原始宗教,你会发现,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间反而十分相似,而与西方并不相同。
若将昂撒人占领北美印第安人的领土视为一种“鸠占鹊巢”,那么这种在文明根基上剽窃和魔改,就是发生在文明领域上的“鸠占鹊巢”。注意这里的定性,西方的虚假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而是“偷天换日”、“鸠占鹊巢”、“转移嫁接”、“附体夺舍”,是在别人已有的东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属于“贪天之功,妒人之能”的那种,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指责我们的话语都没什么创造力,都是自己干过的,将“指称”一换,真相立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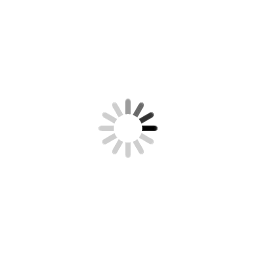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攻占柏林的已经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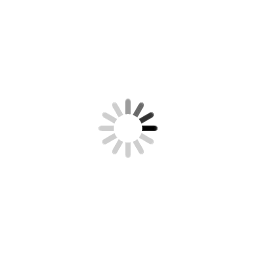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发现了没有,还是“指称”问题,他们的功法根基不是在“实”上,而是在“名”上。
西方文明的认知模式有问题
心理想着“有”,口中却说着“无”,认知与实践相脱节,所以,西方文明体系的矛盾和悖论,从根基上就已经注定了。这就是康德所提出的“二律背反”,这也是西方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渡中必然会看到的问题。
人类的任何认知都是对现实的映射,当我说一个”香蕉“,或你看到”香蕉“这个字时,大脑中都会联想到”香蕉“的图案,而源于我们对”香蕉“的生活经验,看过、摸过、尝过,并以此提炼认知符号,“香蕉”这个词就是一个“索引”或“链接”,用来快速唤起我们对”香蕉“的认知和识别。
如果这种认知出现障碍,就会出现类似失读症或失写症一样的特征,就是那种一个字看久了,原本认识的字自己知道自己认识,但突然一下子读不出来,这是因为……多次重复工作后,大脑累了,罢工了,使得「字形」和「语义」无法很快地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操作过于频繁,系统服务过载,请稍后重试“。过一会儿就好了,若是不好,就是有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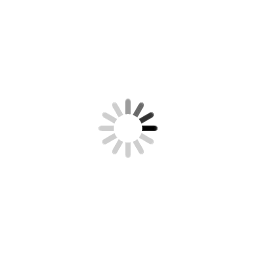
西方的认知模式是,当我说出”香蕉“这个词时,你大脑中想像的不应该是实质”香蕉“的图案,而是我教你的”香蕉“的概念定义(可以理解为一种”香蕉模具“),并借由概念定义而生成一个”香蕉模型“的具像出来。
而这种认知模式下,他们的理论构建与心理实践是相反的。忽略这种内在的认识想像,而搞什么“抽象化”语言表述,不过是盲人摸像罢了,离真相差得远。
人最终是需要通过内心图像来认知的,这是人的认知客观规律所限定的,正常人都是上面那种,而西方的认知模式则是需要经过一层中间层代理中转,搞IT技术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这种方式在IT架构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实现的实践中,最容易发生的是”代理劫持“,我们熟悉的就是某软件的”浏览器默认主页被绑定或篡改“。他们的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基本都有这种痕迹,总是喜欢在“指称”玩心眼,塞私货。
西方人的逻辑就是对事物的简化处理。逻辑的前提是同一,而所谓同一,是削齐拉平的结果,是伪造的。逻辑是为功利目的整理世界的手段。从生成和流变中,整理出实体。把动态的生成流变的世界转化为静态的实体存在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抽象过程,并将这种抽象实体化。所以,对他们而言,数学本身就是纯逻辑理性的产物,是超出宇宙万物的不变法则。
但对中国人而言,不需要如此,数学是从实际需求中出来的,数学逻辑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测量与实验(刻度确定及单位换算),经出于史,经高于史,经归于史,实践总结理论,理论反哺实践,这就是完整的认知过程,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 任何不完整的认知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
西方学术体系的问题,在我看来,比比皆是,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在数学和物理这两个看似最为精确的领域,其他学科领域就更不用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当今世界的混乱无序,与这种名实混乱对立,有着内存的联系。
西方文明的认知问题的根源
西方文明的认知问题源于他们误解了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从而导致形而上学概念的滥用。
”存在“是形而上学永恒不灭的概念,他本质上就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内核。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无论体系多么庞大,其实最终都是对存在一词的探讨。
”存在“ -“being”一词,有时候翻译为”是“、”是者“。”是“本来是一个断定词,判断词。例如“苏格拉底是人”,假如这句话为真,那么苏格拉底指向的对象是不能变化的。实际上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当我说苏格拉底是人的时候,必然存在一个苏格拉底的实体。按照这个存在理论,这个实体必然是存在的,且永恒的。他脱离感官世界,是一个纯粹形而上学概念。
为什么“是”在形而上学之上,成为万事万物的本质规定性呢?因为万事万物的概念,都可以被赋予一个“是”。例如说,上帝是…。苏格拉底是…。
而古希腊文字是表音文字,他本身是不具备表意能力,所以任何词汇,都必须通过“是”去界定。(一系列抽象的符号概念通过某种人为设定的规则组成的描述)
但是这样一来,当“是”后,任何概念被赋予了实体化。无论你认为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概念已经具备了一个实体。只不过人类无法真正认识到这个实体。
…
因为,任何一个概念,如果不加以界定,他就是本体概念。例如苹果,如果不加以界定,那么这句话本质上是空,是毫无意义的。他的概念和存在一词,没有区别。所以两者在人类认识中是有区别的。
但是,当我们提出某个概念,必然已经蕴含着,这个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例如说,当我们说“无”时,我们大脑中想像的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一个“无”的实体,虚无是想像不出来的。
故而,任何概念背后,都必然存在一个“存在”(某个抽象实体),这个存在规定着何以如此存在。
看不懂没关系,最开始我也看不懂,直到我看到巴门尼德提出区分事物的两条路,一条是真理之路(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一条是意见之路(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者存在),真理之路正确,意见之路错误,我就明白这是什么了。
感觉好熟悉啊,在哪里见过呢。
“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这是什么?这是《公孙龙子-名实论》里的话(公孙龙子就是那个提出“白马非马”、“坚白石”的那个),诸子百家之中,有一家叫“名家”,他们是研究名实关系的,也提过许多类似的各种“悖论”。
这句话里,“谓”就是“是”的意思,若把《名实论》中的“实”,理解为“实体”或“存在”,而“名”理解为“概念”,那么这两派的相似度就更高了。考虑到拼音文字的极差的表意功能,我深深的怀疑,若不是流传过程中出了问题,那就是巴门尼德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考虑到他曾经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那么其学问可能是来自古埃及。(古埃及与中国文明的相似性真不是一般的高,以至于部分西方伪史论会认为这是用中国的文献资料所伪造的文明,这里暂时不表。)
在知道其根脚来历,便能搞清楚他们想表达的,以及他们所欠缺的。
名实关系最重要是名实同构相副,而西方文明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名实不同构”,二元对立,名实解耦,导致西方文明在名相符号的构建上放飞自我,“名”实体化了,成为一种特殊的“实”,便有了称此“名”之名,再有了称“此名之名”之名… 以至于无穷“名”,层层代理转换,形成一种“指称地狱”。这种好比“10000…000…”,作为实体的“1”之后,可以有无数个“0”,但那个代表实体的“1”才是关键。
失去了现实参照,西方人的认知应该会始终在二元对立中不断折腾,在语言名相层次内耗,就像沙漠和雪地中迷失的旅人,在不停地无意识打转划圈,只能通过天空的北极星或地磁罗盘,才能辨明方位,走出困境。
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哲学问题的批判吗?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问题在于:
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存在”问题,由于传统哲学混淆了存在和存在者(概念实体与概念实体的具象物),以把握存在者(概念实体的具象物)的方法把握存在,致使存在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传统哲学是一种“无根的本体论”。
要严格区分存在和存在者,存在者是指某种确定的事物和现象,因“存在”而成其自身,存在是使一切存在者得以成其自身的先决条件,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存在具有优先地位。存在的各种意义总是通过存在者来表达。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口里说着“概念实体”,心理想像着“概念实体的具象物”)
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能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应该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即追问存在者存在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存在的意义问题。(如何发生作用,如何与实际相关联)
我们要从存在者入手去追问存在的意义,不能离开存在者去冥想存在。但并非所有的存在都是我们追问存在的意义的出发点,他必须是这样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其他存在物存在的基础。它能够追问存在并且因其自身的存在而使存在显现出来。通过对它的分析能够导致对一般存在的把握。这样的存在者,称之为“此在”。(要解决基本的概念实体的意义问题,比如微积分的本质是分割与累加,数源于测量,“名”源于“实”,逻辑源于简化和抽象)
在人类的思维之中,任何一个概念,不管是什么,人类总会有一个指向性,一定会把这个概念实体化。当我们提出某个概念,必然已经蕴含着,这个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例如说,当我们说“无”时,我们大脑中想像的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一个“无”的实体,虚无是想像不出来的。
我们的感官,分明看到是流变的世界,而我们的理性却总是赋予一个实体概念。两者的矛盾,构成了理性和感性思维的矛盾。
而绝对的存在和绝对的无,本质上是一回事。因为绝对的“无”无法表述任何事物,绝对的“有”,也无法表述认识事物。所以,绝对无实质上表述的是在人类思维之外,是超越逻辑的存在。他和存在是一体两面。
因此,任何有限的存在者,他一方面要被绝对存在(绝对的有)所规定,一方面又要被绝对的虚无(空无与非存在)所规定。
绝对的有,赋予我们一个实体化倾向(凡物必有其名相)。而绝对的无,造就了流变的表象。(事物和时空,时空反衬运动)
故而,一切存在者,都是处于绝对的有和绝对的无之间。如何认知和把握“绝对的有和绝对的无”这种超越逻辑的一体两面的“超越者”(找不出其他词语了),便是西方文明未来的命脉所在。
这是我按西方哲学的思路给西方文明提出的建议,不明白这一点,总是拿无限当有限,将“绝对”化为另一种“相对”,把上帝置于宇宙万物的对立面,在这样的世界观指导下,西方的未来注定会在与世界的不和谐斗争中分崩离析。
结尾
之所以要从无穷问题开始讲,是因为对“有限与无限”与“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是入道的门槛,而 1=0.99999…(实无穷与潜无穷)更是理解宇宙实相的关键,这一点非常重要。